文化中國行|我市博物館各出奇招,文物說明牌不再眾口難調
2025-07-10 06:47:53 來源: 重慶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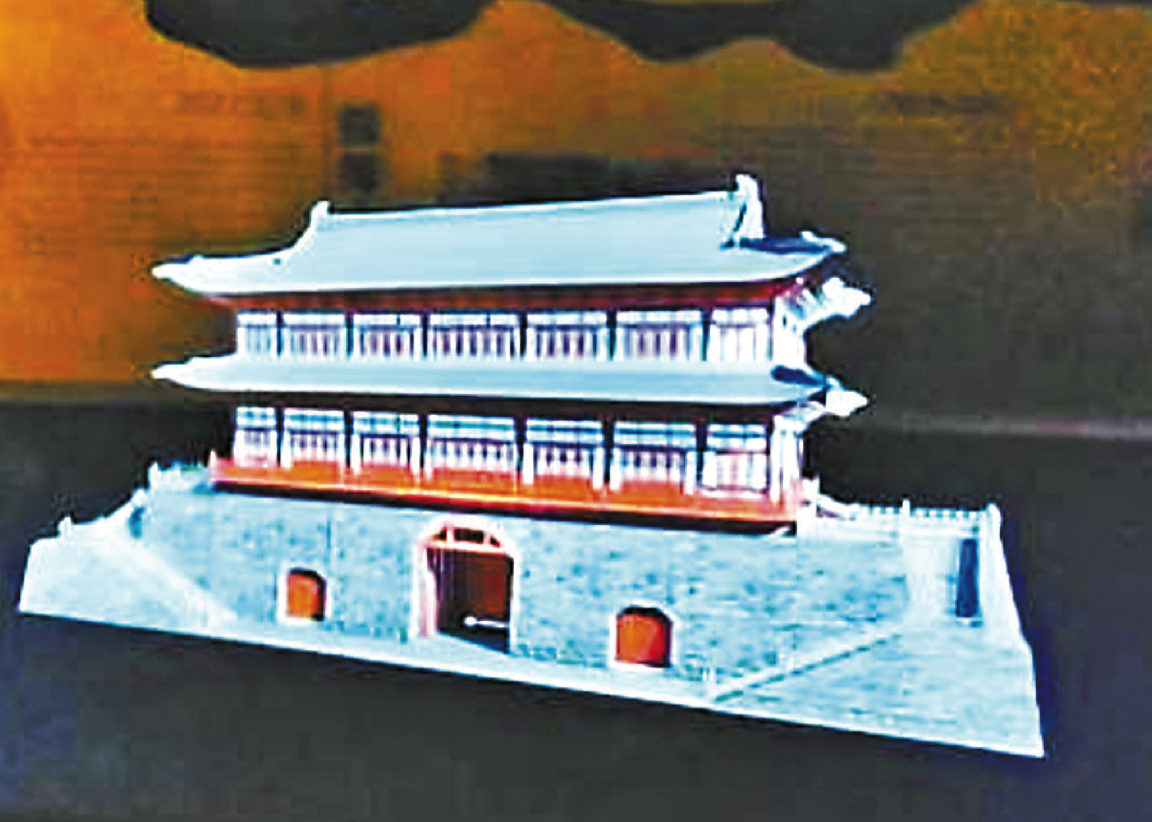

為迎接暑假,眾多博物館根據自身特色,策劃推出形式多樣的陳列展覽。然而有觀眾反映,一些文物說明只有三言兩語的簡單信息,無法了解其豐富內涵,影響觀展感受。
文物說明是觀眾了解展品最直觀的途徑之一,相當于自我介紹的名片,那么這張名片上的文字該如何表述,才能更好地拉近觀眾與展品之間的距離?
7月8日,記者走訪了我市部分博物館,打探它們在文物說明牌上取長補短的創新舉措。
文物說明牌眾口難調
當日,記者走進我市一家博物館看到,該館為了方便觀眾了解文物故事,在重點文物下方擺放了超過200字的詳細文物說明,但受限于文物說明牌尺寸,這些文字密密麻麻地擠在了一起。
展廳里,家住九龍坡的市民劉芳宇一邊大聲在父親耳邊讀著說明牌,一邊拽著想要去看下一個文物的兒子。“父母年齡大了,想看清楚這些文字確實不容易,我知道博物館里不該大聲交談,但遇到他們感興趣的文物,又不舍得讓他們錯過。”看著已經跑遠的兒子,劉芳宇話語里帶著些許無奈,“娃兒看久了就沒得耐心了,一路走馬觀花圖個新鮮,文物的故事背景不愿意再了解。”
“看多了,莫說娃兒不愿意看,我一個大人都覺得累。”一旁觀展男士的一句笑言,化解了劉芳宇的尷尬。
劉芳宇的尷尬被化解了,可博物館說明牌的尷尬又該怎么破?這并不是一兩家博物館里的個別現象,而是全國大多數博物館面臨的難題。
“青銅器的說明牌上好多生僻字既看不懂,又讀不出,孩子問我,我也不知道該問誰。”
“說明牌上就寫了個文物名字、尺寸、年代,其他信息一律沒有,這樣的展覽讓人怎么看?”
“我們不是專業學者,文物說明牌上一堆專業文字,對普通人太不友好了,讀個說明牌還要找百度。”
……
面對觀眾對文物說明牌的眾多需求,重慶市博物館協會會長程武彥認為,從眾口難調到眾望所歸,博物館從業者才是真正的破局者,“博物館的文物說明不用局限于說明牌的方寸之間,文字說明也應滿足不同觀眾群體的多樣化需求。”
文字讀著不過癮,手繪圖畫來添趣
如何破局?重慶各大博物館早就開始了各自的創新嘗試。
2024年,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推出“人間有味是清歡——明清畫境中的生活景象”展覽,其中的文物說明牌就得到了眾多網友的一致贊譽。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看懂展覽中的國家一級文物《唐寅臨韓熙載夜宴圖》,策展人專門在文物旁邊制作了一塊巨大的手繪“黑板報”,將唐寅對原版《韓熙載夜宴圖》的修改用文圖的方式一一標出。
這幅巨大的文物說明牌,也成為了展覽中最吸引觀眾的地方。看一眼圖畫,讀一段文字,再比對著原畫找一找,成為觀眾的一大樂趣。
為何會想到制作這樣的文物說明牌?
展覽策展人王麒越道出了答案——抓住觀眾的好奇心。“很多人都知道這幅國寶是唐伯虎臨摹前人而成的畫作,那么大家一定好奇,唐伯虎有沒有在里面加入自己的小心思。恰好,唐伯虎確實這么做了。于是,我們就想到,把唐伯虎這些小心思單獨提出來,和原畫進行對比,增加觀眾看展的興趣,也讓大家能夠讀到更多文物故事。”
在王麒越看來,只有拉近文物藏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才能讓觀眾同博物館里的這些“歷史見證者”有對話、有共鳴。
針對不同需求推出文物說明
“自然博物館的觀眾群體以青少年為主,所以我們決定,借助AR技術,為化石標本加上‘血肉’,由它們來講述自己的故事。”重慶自然博物館館長高碧春說,博物館不僅努力讓文物說明更加生動,而且還針對不同年齡段的觀眾推出了數個版本的文物說明。
高碧春介紹,每一位恐龍明星的故事都不同。比如,合川馬門溪龍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完整的巨型蜥腳類恐龍化石,將承擔全景式講解化石發掘的故事,“我們計劃通過AR技術,將近40噸的化石發掘過程再現在觀眾眼前,同時,這具體長24米的龐然大物,也將穿越時空而來,出現在觀眾面前。”
“我們發現,對幼兒及小學年齡段的觀眾來說,他們更喜歡看到以動畫片為主的講解。中學到大學的觀眾,則更喜歡聽專家的詳細講解和看電腦合成恐龍的科普內容。”高碧春說。
基于此,重慶自然博物館推出了3個版本的內容。其中,青少版通過可愛的動畫形象、有趣的動畫場景,生動地還原標本的故事。亞洲象、雙角犀鳥、草原犬鼠等一眾貝林廳里的“明星”都在此列。
而普及版則以3D形象,全方位展現化石標本背后的故事。上游永川龍、重慶江北龍、許氏祿豐龍等一眾恐龍廳里的大明星,被劃歸到了普及版之中。
在專家版中,高碧春將現身,親自為游客們進行專業講解,讓游客更加清晰地了解精彩紛呈的動物世界。
在高碧春看來,文物標注和文字說明,是參觀者獲取相關信息最直觀、最簡單的方式,讓說明牌兼顧知識性和趣味性并生動起來,一件件文物也就變得具體而鮮活。
重慶正在探索無障礙觀展
秦良玉的刀、青銅鳥形尊、南宋金腰帶……在這個展覽中,觀眾不僅能近距離欣賞展品,還能上手摸一摸它們。三峽文物科技保護基地正在通過這樣的嘗試,深度聚焦博物館與觀眾的互動議題。
為何要做這樣的探索?展覽策展人喻子曦坦言,是為了打破殘障人士特別是視障人士與博物館的距離——通過復制文物,讓文物本身成為一塊可以觸摸的說明牌。
展覽中的無障礙展線實驗將無障礙設計的理念與博物館策展的方法論結合起來,通過對無障礙設施(無障礙導覽圖、盲文展簽、可觸摸展品等)、無障礙信息交流、無障礙服務等多個板塊的設計提升,保障更多人群參觀動線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滿足其在展覽及周邊環境中行、聽、看、休息和交流等方面的活動需求,營造出博物館場域下的無障礙參觀環境。
那么復制出來的展品與文物原件有區別嗎?
喻子曦說,從外形觀感和觸感上來說完全沒區別。為了能讓觀眾真實感受文物本體的手感,無論是文物的花紋,還是文物身上的斑斑銹跡,都和原件沒有差別。
除了“無障礙展線實驗”探索無障礙參觀的可行性之外,展覽還特別設置了另外9個引人深思的互動實驗——“熱門問題回復實驗”解答觀眾最關心的熱點問題,“展品提問實驗”鼓勵觀眾以展品視角發問,“觀眾問題墻”與“博物館問題墻”可讓雙方的聲音被聽見。這些實驗不僅趣味橫生,更富含深意,旨在激發公眾對博物館文化的深度思考與參與熱情。
面對文物說明牌眾口難調的難題,重慶的博物館正以創新破局:或借生動圖畫放大細節,或用科技分層講述故事,或憑觸感復制品消除壁壘。這些實踐的核心,在于跳脫方寸之間的局限,以多元手段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讓孩童看得有趣,讓長者看得清晰,讓視障者得以觸摸歷史的溫度。當文物說明不僅是冰冷的標簽,而成為開啟對話、激發共鳴的鑰匙,博物館才能真正成為連接古今、服務大眾的文化殿堂。
責任編輯:譚周








 發言請遵守新聞跟帖服務協議
發言請遵守新聞跟帖服務協議

